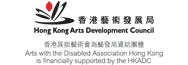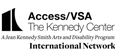日期:2012年10月29日
報章:南方都市報
我們可以憑藉光影的交錯看到一朵花、一片雲的美好,我們可以在劇場裡聆聽音符的美妙,我們可以跳躍、奔跑、扭轉、舞動來訴說情緒……如果,我們看不到、聽不到、走不了呢?你還能與攝影、音樂、舞蹈這些文化活動發生交集嗎?你還能融入到一個正常人的文化生活中去嗎?單單的一個殘疾人通道與洗手間只不過是物理上可見的通路而已,對於一個殘疾人士而言,拿起單反、走進劇場,甚至是站在舞臺上,走入到完全平等的社會中去,無疑是需要更多的精神與靈魂上的通路。
在香港,就有這樣一撥人,他們致力於讓殘疾人士與健康人士融洽共處、相互扶持,而他們溝通的語言,是藝術。半個月前,“多一點藝術節”在香港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1藝廊舉行。3D立體攝影作品、玻璃製品、陶藝製品、玻璃創作作品、撕紙作品……你難以想像這會出自一些傷殘人士之手。在10月初開幕的香港首個由聾人主導的戲劇項目“香港聾人戲劇節”,也上演12場令人耳目一新的戲劇,戲劇節一直演至11月,讓不同類型的觀眾有機會體驗絕少在香港上演的劇種。
視聽障人士也能玩藝術,讓公眾忘卻其弱者標籤
陳淑芳穿著一條黑裙子,套了件今年最流行的絳紫紅西服,站在“多一點藝術節”展場的門口,等待著嘉賓與觀眾的入場。
有人習慣性地、禮貌地遞了張名片。她笑了笑,說,我看不到。她也聽不到 如果你說抱歉的位置距離她很遠的話。她只能在很近很近的地方觀察人的口型,以確定對方在說些什麼。她是一個視聽障人士。但她這次來,是為了介紹她在展覽中展出的幾件展品。
這是一條魚,一條陶瓷燒制的蒸魚。在“陶藝大廚”的工作坊中,陳淑芳第一次接觸到了藝術創作。當然,除了她之前曾經參加過的一個捏泥人活動。她心裡還是有些惴惴的,她很擔心會遇到跟當時一樣的情形。“那個老師很是不高興,說八歲小孩都比我捏得好!”陳淑芳說,“所以,一坐下來,我就跟工作坊導師說,我不行的。我看不到。”
陳淑芳當時真的是什麼都看不到。因為,她面對的是白色紙上放著的白色瓷碟。這種沒有立體感可言的物品佈置方式,對於原本就不能很清楚地識別顏色的她來說,簡直就是對她的考驗。但導師很快就找尋到能夠幫助她的方法把黑色底板放在白色紙上,用不同的顏色製造強烈反差。
這只是問題的開始。陳淑芳還需要進一步分辨顏色。這對於只能模糊看到黑白灰三種顏色的她而言,簡直就是有些異想天開。工作坊導師拉著她的手,逐一顏色地摸過去,“這是藍色、這是紅色、這是黃色……”然後,等著陳淑芳的,就是一層一層的顏色塗抹,直到顏色鮮豔到自己都可以看到。於是,她得到了這條魚。
陳淑芳把這條“蒸魚”當成自己的寵物,她不僅帶著她去給自己的親朋好友看,還帶著她去逛公園,去小湖邊“放生”,告訴這條“蒸魚”在湖裡有很多它的夥伴。“這條魚像是賦予我重生的生命,我還要帶著它去周遊世界。”或者說,她自己就像是這條藍色的魚,跳躍過了她自己潛意識中對殘障人士與藝術世界默認的“鴻溝”。
“我是行的。”陳淑芳在整個導覽過程中,不論是介紹自己的“蒸魚”,或是撕紙、或是玻璃製品,她總是不停地說這句話。而在接觸這個之前,她認為,看不到顏色是不能制陶的,看不到紙張的細微間隙是撕不了紙的,就更不用說透明的玻璃了。
除了陳淑芳,還有很多與她一樣的殘障人士的作品在這裡展出。塑膠彩繪、油畫、立體攝影製作……很多作品功夫精細到讓人懷疑這是否真的出自殘障人士之手。因為,在這些作品下面,只有作品名與創作者名,並沒有標注究竟是身體哪一方面不便。“我們相信,人人生而不同,我們尊重每個人的不同。但是,在傳統的文化上,很多人都是一聽到殘疾人士、展能藝術就一定有一個標籤,覺得他們很可憐,需要救助,公眾看到的就是他們的弱點。我們就是想公開地讓公眾知道,不要只看到他們殘疾的標籤,而是要知道大家只要有平等的機會去培養藝術潛質,每個人都可以在生命中、藝術中有發展。”“多一點藝術節”主辦方香港展能藝術會執行總監譚美卿在提及到署名問題時強調。
傷健也能平等溝通,共融的語言叫藝術
高便蓮,是展能藝術會“多一點”玻璃創作工作坊的導師。2003年,由於參加一些課程接觸了展能藝術會。她不知道殘障人士究竟能否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從事這些創作,雖然“沒試過,不知道”,但她不拒絕。
“其實,玻璃創作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它會用到火槍燒制。”但這並不妨礙一些如陳淑芳一樣的視障人士參與。
對於導師而言,首先需要的就是找一些最簡單的東西去瞭解學員的能力,然後再設計課程配合。“這種配合並不困難,即便是教普通人也是需要分年齡進行分別教育的,對於這些不同能力的朋友而言,導師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將固有的方式與認識框架套在學生身上,去評價。”在高便蓮口中,傷健人士之間的溝通,並不存在著隔閡,導師的配合就是不打擊自信,給予安全感的同時,再去開發多些創意的可能。
而這種安全感與自信也正是陳淑芳能夠做出這一系列作品的原因。“對於視障、聽障的人來說,我們需要環境的平靜,特別嘈雜的環境會讓我們感覺到混亂,我們需要可以觸摸的安全,如果手上摸不到,就會感覺到無助。”陳淑芳說。
事實上,在這種自信與安全的共融環境的建構下,殘障人士所表達出來的藝術能量也讓高便蓮驚訝。看不清東西、分辨不了色彩的陳淑芳竟然可以在兩個拇指大小的透明玻璃瓶上作畫。“他們的能力並不是如普羅大眾所想像的那樣。”高便蓮說。
傷健共融也會給健康人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
在香港,共融社會似乎已經漸漸成為一種共識。十字路口的盲音、地鐵的點字導覽、殘疾人通道、廁所……即便,你不是一個視障人士,你也可以親身去體驗完全黑暗的世界。在美孚的“黑暗中的對話”,你就可以進入到一個完全黑暗的影院中,摸索著坐下,聽銀幕上的演員對話。但一旦演員沉默,你便會慌了神,究竟這銀幕上在上演著什麼?這時候,顏素茵或許會幫上你。
顏素茵是一名口述影像員。5年前,她因為工作上需與不同能力的創作人(殘疾人士)溝通相處,便順理成章想學手語、點字和口述影像。“我那時負責為視障音樂人、作家汪明欣安排和進行公眾教育活動,時常要向明欣描述周遭事物,記得試過有一次要即時口述歌唱比賽現場實況兩個多小時,因為不懂口述影像技巧,長時間高度集中描述,感覺力有不逮,所以決定開始學習。”
不過,顏素茵卻發現在香港學習口述影像的途徑並不多。“據我所知,除了香港展能藝術會曾於2008年開辦口述影像工作坊和近年辦過幾次為義工而設的口述影像導賞訓練外,便只有香港盲人輔導會2011年香港電影口述影像發展計畫開辦有系統的口述影像培訓課程。在資源運用層面,獲培訓的學員數目不多,學員能持續服務的更少。”顏素茵說,“這也許是培訓工作仍在起步階段,本地的口述影像服務尚未發展出成熟的互惠模式的緣故吧。”
顏素茵在努力地尋找不同的看的角度。她和同學們曾經在課堂上,為了是用撫尺還是驚堂木去描述一個影像中出現的實物而爭執,老師卻一語道破“可以說,那是一塊黑色的木頭”。作為一個健康人士,她總是想讓自己儘量處於傷殘人士的角度去“看”事情。她總是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看不清楚(年老了)、看不到(失去視力了),這個表情、動作、場景、影像,我會希望聽到怎樣的描述。”
在她看來,視障與非視障人士欣賞作品時,同樣需要“看”,只是“看”法各有不同。而對於非視障人士而言,口述影像也無疑在提供另外一種“看”法。“有一個健康觀眾聽過口述影像後告訴我,他沒有想過原來作品可以這樣看。這讓他能夠通過第三者對圖像、裝置的描述説明自己多一角度地注視作品的重點。”他說的有句話讓顏素茵印象深刻,“我們有時以為我們有正常的視力,但往往可以看到的,卻沒有看到”。
去年,顏素茵從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畢業。在畢業展上,她開啟了學界設有通達服務的先河。“我們一班同學抱著"Artsareforeveryone"的理念,為畢業展覽提供了點字和口述影像服務,並設導賞團予社福機構。”
主流文化場館日漸通達,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接觸藝術
事實上,我們在“多一點”藝術節上,就可以感受到顏素茵口中的這種通達服務。就是在入口的資料發放處,這裡與其它展覽場館有些許的不同,這裡除了配有中英文資料之外,還有厚厚的一疊點字資料,還有一些口述影像的導覽設備提供。在展品的旁邊,也有一張或者幾張觸感圖,告訴視障人士作品圖片的色彩分佈、線條走向、構圖佈局。
“我們講究的是藝術通達。這不僅是泛指交通安排、場地上的無障礙設施,更包括視覺及聽覺設計上的配合讓不同能力人士共融參與文藝活動。”譚美卿說,“無論殘疾人士及長者,其實都應有與其他香港市民一樣的平等機會去參與文化生活。他們與其他大眾一樣,在藝術及文化活動方面都有同樣的需求及興趣,以提升生活質素。聽不到的,我們可以提供字幕引導,看不到圖像的,我們會做口述影像,還有點字觸感,讓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去接觸藝術,去培養藝術潛質。”
現在這種藝術通達服務已經慢慢在敲開香港主流文化場館的大門。例如,香港藝術館、尖沙咀歷史博物館,都已經在逐步接受通達服務。這些讓陳淑芳們從一開始不敢去接觸社會、參加文化活動,變得慢慢有信心逐步地去欣賞藝術,甚至自己也參與到藝術創作當中。“西方國家,例如美國已經在藝術通達上做了二三十年,並立法保障,但在香港,這才剛剛起步。其實,香港人口日漸老化,迫在眉睫的表演場地以及藝術節目的通達問題都應受到正視。”譚美卿說。